
1962年版电影《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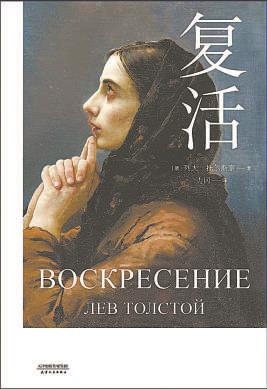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复活》
“值班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顿时从牢里冲出一股比走廊里更熏人的臭气。值班看守冲里吆喝:‘玛丝洛娃,过堂!’随即又掩上牢门,在门外等着。”
“即使在监狱的院子里,也有风从城外刮来的清新爽人的野外空气。可是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充满伤寒病菌,充斥着粪便、焦油和腐败物的恶臭,令任何人一进来,立即就感到忧郁和烦闷。虽然女看守闻惯了这污浊的空气,可是她从院子里一进来,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她一进走廊,顿时感到疲倦,昏昏欲睡。”
这是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开篇的文字。这段文字在1962年版和2001年版的电影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对比小说和电影,两者各擅所长,文字更自由,主观色彩更浓郁,而电影用画面的形式展现,更直接而形象。
1.
1887年6月的一天,法官柯尼到托尔斯泰家中做客,他对托尔斯泰讲述了自己亲手经办的一件案子:一个贵族青年在出席陪审时认出被诬告偷了客人一百卢布的妓女原来是几年前被他强占后抛弃的姑娘,这个贵族青年顿时觉得良心不安,要求法官带信给女犯,表示要娶她为妻。后来女犯在狱中染病身亡,贵族青年也不知去向。这个故事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了他创作《复活》的素材与灵感之源。
从1889年到1899年,这部小说的创作时间持续了十年。托尔斯泰起初为这部长篇小说起的名字叫《柯尼的故事》,数易其稿之后,才定下了篇名《复活》,隐喻一个人泯灭的良知在某种精神力量的感召下可以获得重生。“复活”点出了这部小说的主题,作家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
《复活》围绕少女玛丝洛娃被诬犯杀人罪,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决定为之奔走申冤,上诉失败后又陪她去西伯利亚流放,这一条主线讲述的动人故事,情节曲折跌宕,为文字化为影像提供了坚实基础。
玛丝洛娃原本是一对有钱姐妹人家的半养女半奴婢的姑娘,后来被这对有钱姐妹的侄子聂赫留朵夫公爵诱奸,致使玛丝洛娃怀孕被辞,生活没着落的玛丝洛娃最后沦为一名妓女。一次,玛丝洛娃为了摆脱一名商人的纠缠,就在喝的酒里下了安眠药,商人“因饮酒过量引起心力衰竭而死”。结果,玛丝洛娃与另两位妓院人员被疑为盗窃商人钱财而把砒霜放在商人的酒里致使商人丧命,并接受法庭审判。案件审判之际,聂赫留朵夫正好作为陪审员出席法庭,认出了十年前被他诱奸的玛丝洛娃……
聂赫留朵夫在跟随玛丝洛娃流放的过程中,终于发现自己一直以来的“高尚”举止失去了目标,突然发现自己从来不曾、也永远不能拯救玛丝洛娃,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资格,没有这样的力量。他甚至没有这份用心——所谓拯救玛丝洛娃,并不是真正出于同情,而仅仅是想让自己从过往的生活中逃脱出来,让自己找到高尚的理由。正如1962年版电影中玛丝洛娃的那句锥心之问:“你想用我拯救你的灵魂?你玩弄了我还不够,死后还想利用我上天堂?”
玛丝洛娃是怎样被错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刑四年的呢?这在小说和电影中都是主线,是推动作品情节发展、展现人物品性及时代风貌的关键所在。
2.
开庭前的晚上,当书记员通知公诉人开庭审判玛丝洛娃毒死人命案时,公诉人因为给一个同事送行,喝多了酒,又玩纸牌……“恰巧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目前想去草草地看一遍”,就要“永远站在他的地位的高处,也就是探索罪行的心理意义的奥秘,揭露社会的痈疽”了。以致因陪审员的失误,认定玛丝洛娃有罪时,让公诉人感觉“出人意外地成功了,不由得暗暗地高兴”。轻率与轻忽,让这起案件的审判在初始阶段就出现了致命的错漏。
俄国在1864年实行司法改革,建立了陪审员制度。小说详细介绍了审理玛丝洛娃案件的陪审员:五品文官、退役上校、二等商人、上尉、商人、年老的劳动组合成员、中学教员、店员,而聂赫留朵夫的身份是近卫军中尉和公爵。庭审之后,法庭交由陪审员决定的主要问题是:三名被告是否犯有抱着劫夺商人钱财的目的,蓄谋杀害他的性命。托尔斯泰对这一背景的描述通过庭长“开导”陪审员们来予以展现:“假如你们(陪审员)认为被告们有罪,你们就有权利裁定他们有罪;假如你们认为被告没罪,你们就有权利裁定他们没罪;假如你们认为他们犯了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你们就可以裁定他们犯了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他要求陪审员们凭着“社会的良心”作出判断,这一不可捉摸的标准加上对玛丝洛娃先入为主的偏见,将玛丝洛娃的命运导向了悲剧的结局。
陪审员们讨论法庭及庭长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玛丝洛娃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首席陪审员、熟悉一切讼案的五品文官尼基福罗夫坚决主张玛丝洛娃既犯了毒死人命罪,也犯了盗窃罪。而其他人则有的不同意,有的摇摆不定。最后,首席陪审员似乎接受了大家的意见,提出“裁定玛丝洛娃犯了毒死人命罪,可是没有劫夺钱财的意思,她没有盗窃商人的钱财”。首席陪审员以为这样表述,玛丝洛娃也就没罪了,而且还不忘添上一句:“是的,没有劫夺钱财的意图。”但是,陪审员们却没有提出最关键的一句:“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
玛丝洛娃没有偷窃,也没有劫夺钱财,同时又没有任何明显的目的而毒死了一个人,但是,陪审员们最终作出的裁定却导致了一个荒唐的结果——托尔斯泰的描述是“等于判她去做苦工而她又没有罪”。
原本为“实现公正司法”而实行的法庭陪审员制度,却被陪审员们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定的情况下,就使无辜的玛丝洛娃及其他两位同伴入罪了。深究起来,还有这样一些因素:一是讨论案件的时候,身为陪审员的退役上校闲扯的时间太长,占去了大家讨论案件的时间;二是聂赫留朵夫当时过于激动,竟没有注意到漏掉了一句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之类的保留意见,以为有了“没有劫夺钱财的意图”就消除了判罪的可能;三是坚决认为玛丝洛娃无罪而且头脑一直清醒的中学教员格拉西莫维奇,在首席陪审员重读那些问题和结论的时候,他正好出去了,未能及时纠正这一错误。
当然还有法官、庭长的问题,“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执法者各有各的心思,随随便便将一个受害少女玛丝洛娃判刑。”庭长因为要去约会一个从瑞士来的女人,想尽快结束庭审,所以他的总结发言根本就没有一一答复陪审员们提出的问题,只是依样画葫芦地说:“是的,她犯了这样的罪,但是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他本该发现逻辑上的瑕疵,但是他根本心不在焉。
按照制度设计,当陪审员们作出错误或极矛盾的结论时,庭长本应引用“法庭倘若发现裁决不公,就可以取消陪审员们的决定”,然而这一点被轻易忽略了。之后庭长征求其他两位法官的意见,而一位法官竟然在占卜般谋算:要是他相加的数字能被3除尽,就同意陪审员的意见。虽然他的占算没有被3除尽,可“他心肠太软,还是同意了”,当然他同意的是一个逻辑混乱的结论。另一位法官因为开庭前正与老婆生气,使他变得愤愤不平,情绪无处宣泄,便“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坚决地说:“报纸本来就已经在纷纷议论,说陪审员们总是开脱罪犯;如果法官也开脱罪犯,那它们会怎么说呢?”庭长为了赶快结束庭审迁就了这位法官,作出了让“所有法庭工作人员,包括书记官、律师们以至检察官在内都露出惊讶神情”的判决:玛丝洛娃无罪却被发送西伯利亚服苦役刑四年……
这个荒唐的结果,使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在很多读者心中,也获得荒诞主义文学大师的称号。
3.
《复活》对俄国社会尤其是司法腐败的揭露和批判可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托尔斯泰认为社会如此腐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质”,在他看来,每个人身上仿佛都有“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对抗。“兽性的人”占了上风,人就作恶;“精神的人”取胜了,人就向善,而人可以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作者的这些思想及其评述在电影里无法完整地传达出来,因为大段的评述——包括很多电影中无法展现的心理活动——会削弱电影情节的紧凑和吸引力,而电影情节上的紧凑带来的吸引力却是小说无法比拟的,孰优孰劣,全赖读者及观众的选择与评价,他们是最终的裁决者。经典文学名著及其改编的电影,其实相辅相成,各有所长。
值得一提的是,在托尔斯泰生活的时代,他所倡导的通过忏悔实现救赎之路,是一个几乎无法行得通的死胡同,因为他“抹煞了造成社会灾难的根源是统治阶级的剥削本性”。不过,托尔斯泰对人性的探索以及人性完善的执著,依然是每一个一心向善的个体不懈追求的道德巅峰。
“尽管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千方百计将他们聚居的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用石头覆盖地面,不让地上长出任何东西,尽管出土的小草都被清除,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的浓烟四处弥漫,尽管树木被滥伐,鸟兽被驱散,但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仍然是春天。
“阳光和煦,小草复活,只要除根不尽,它们就生长、发绿,不光在林荫道的草地上,而且在铺路石板的夹缝中。桦树、杨树、稠李长出黏稠清香的嫩叶,菩提树鼓起一个个饱胀欲裂的新芽。寒鸦、麻雀、鸽子怀着春天的喜悦,已经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被阳光照暖的苍蝇也在墙脚嗡嗡作声。草木也好,鸟雀也好,昆虫也好,孩子也好,全都生机勃勃……”
让我们回到小说的开头,让整部作品中的沉郁、荒诞褪去,让我们仔细领悟托尔斯泰心底的那抹亮色。无论时代如何跌宕起伏,无论各种思潮如何针锋相对甚至挥戈相向,这抹亮色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该是自然的破坏者,不该是文明的背叛者,不该是良善的毁灭者。








